凡事要自然而然
发布时间:2024-07-01 01:15:05作者:楞严经在线网
凡事要自然而然
本焕长老在一次开示中向信众讲解用功修行的方法,其中有一句:“无心用功并不是说没有心,像木头一样,它只是不起‘去用功’的念头,它的用功是自然而然的,不需要有意着念,它往往是不参自参,不疑自疑,不照而照的。”这种不起用功的念头实则是一种习惯,一种自动自发的习惯。
这种习惯的发生就像植物生长、四季轮换一般,不需要特别的决心,刻意地努力,因为自动自发地生长、轮换就是生活、生命本身。本焕长老要人用功,却要人不起“去用功”的念头,其实就是要人把用功当成生活的一部分,让人能在一言一行中自然而然地踩在用功的点上,从心底由衷地流露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天性。在他看来,这种自然而然地用功才算是符合人之本性的。
人本是自然之子,但在社会进程中,人一方面得以升华,以文化区别于动物,同时也被社会所异化,从而表现出许多非自然的属性,在商业社会中,这种异化尤为明显
停下工于心计、追逐名利的脚步,习惯悠然漫步,习惯以单纯自在的心态,乐享自然中最原始的一切,从每一种花草身上看见美丽,从每一阵清风中听到时光的低吟浅唱,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回归自然的淳朴,便能超脱现实的烦恼之上。因此那些超脱红尘之外的得道者,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风道骨,反而是以天为盖、以地为席的自然之子。
当有人问在山中居住、以野果果腹的高峰妙禅师为什么喜欢吃野果,为什么不梳头发时,他反问道:“山珍海味能比野果好吃到哪里去?我连烦恼都没有,还需要梳理什么头发呢?”
“你一年到头就这身衣服,为什么不备一套换洗的呢?”
“佛法慈悲、道德这身衣服就足够。”
“你总要洗洗澡吧?”
“我的心一干二净,不需要洗澡。”
“你没有朋友,没有爱人,不觉得孤单吗?”
高峰妙禅师指指外头说:“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朋友。”
俗人以为高峰妙禅师的修行是徒然,高峰妙禅师却笑俗人忽视自然的愚钝。花香沁醒心灵,草绿清亮视线,绿荫山峦放松心境,一野果、一掬泉都是原生态的营养。一心参禅,与大自然融为一体,享受清静、新鲜的生活滋味,实在是难能可贵。自然开启人的心灵、陶冶人的情操,久居闹市,心久系名利,人实际上活得很累。荣华富贵、名声赞誉都是表面的东西,月明风清时,人立于月下,会突然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可笑、很荒唐。整日费尽心思与人争斗,得到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烦恼,何必要这样为难自己?
不如将争强好胜的心放下来,到自然的怀抱中沐浴清风,攀登高山,放歌旷野,这种看似休闲、放松的方式,其实是在修心上用功夫。功夫用得不着痕迹,却轻松自然地让心灵放松了戒备,感受到了欣悦。
相比于这种不刻意、不起念的修行,那种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的求取,反而会流于表面、形式,致使努力的人和真正的开悟擦肩而过。
唐朝龙潭崇信禅师,跟随天皇道悟禅师出家,数年之中,打柴炊爨,挑水作羹,不曾得到道悟禅师一句半语的法要。自认为一无所获的他问禅师:“弟子自从跟您出家以来,为什么不曾得到您的开示?”
道悟禅师听后回答道:“自从你出家以来,我未尝一日不在向你传授修道心要。”
“弟子愚笨,不知您传授给我什么。”崇信讶异地问。
师父并没有理会他的诧异,只是淡淡地问:“吃过早粥了吗?”
崇信说:“吃过了。”
师父又问:“钵盂洗干净了吗?”
崇信说:“洗干净了。”
师父于是说:“去扫地吧。”
崇信疑惑地问:“难道除了洗碗扫地,师父就没有别的禅法教给我了吗?”
师父厉声道:“我不知道除了洗碗扫地之外,还有什么禅法!”
崇信禅师听了,当下开悟:禅就是生活,能够自然而然地生活,本身就是一种参禅悟道的修行。吃粥、打扫,看似平常,却像正中靶心的箭矢一样,无限接近修禅之道。能用心静静地聆听生活的不语,领悟其中微妙的禅机,何尝不需要一种功夫呢?
现实生活中的禅法,是将佛法“生活化”,又用佛法“化生活”,在生活中实现禅悦,在禅悦中享受人生,保持一颗本色之心,遇山则高,遇水则低,随顺自然。
迎着每天八九点的阳光,站在窗边手捧一杯醇香的咖啡,看着匆忙的脚步路过街边,有条不紊地开始一天的工作,自是一种徐生慢活的践行;工作八小时中抽一点时间,伸伸懒腰,看看探入房间的嫩绿枝条,放眼被风放牧的天边云朵,紧张的心松弛下来,然后以一种全新的开始继续投入工作,何尝不是一种自然的领悟;工作结束后,不在电视虚像中放空思想,而是手捧书卷,靠于窗边,轻松温读,早早入眠……
以上这些没有任何养生理论的指导,只是佛说“禅宗不立文字,直指人心,似乎有迹可循,却又如月穿潭底,了无痕迹”,所谓修禅、用功,不过是还原生活的原貌,规律、简单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、工作学习。果真这样做了,不经意间遇到花开,微笑会悄然攀上嘴角。
本焕长老在一次开示中向信众讲解用功修行的方法,其中有一句:“无心用功并不是说没有心,像木头一样,它只是不起‘去用功’的念头,它的用功是自然而然的,不需要有意着念,它往往是不参自参,不疑自疑,不照而照的。”这种不起用功的念头实则是一种习惯,一种自动自发的习惯。
这种习惯的发生就像植物生长、四季轮换一般,不需要特别的决心,刻意地努力,因为自动自发地生长、轮换就是生活、生命本身。本焕长老要人用功,却要人不起“去用功”的念头,其实就是要人把用功当成生活的一部分,让人能在一言一行中自然而然地踩在用功的点上,从心底由衷地流露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天性。在他看来,这种自然而然地用功才算是符合人之本性的。
人本是自然之子,但在社会进程中,人一方面得以升华,以文化区别于动物,同时也被社会所异化,从而表现出许多非自然的属性,在商业社会中,这种异化尤为明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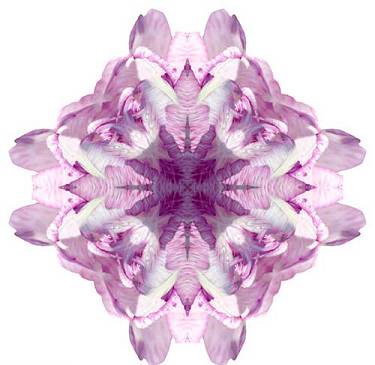
停下工于心计、追逐名利的脚步,习惯悠然漫步,习惯以单纯自在的心态,乐享自然中最原始的一切,从每一种花草身上看见美丽,从每一阵清风中听到时光的低吟浅唱,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回归自然的淳朴,便能超脱现实的烦恼之上。因此那些超脱红尘之外的得道者,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风道骨,反而是以天为盖、以地为席的自然之子。
当有人问在山中居住、以野果果腹的高峰妙禅师为什么喜欢吃野果,为什么不梳头发时,他反问道:“山珍海味能比野果好吃到哪里去?我连烦恼都没有,还需要梳理什么头发呢?”
“你一年到头就这身衣服,为什么不备一套换洗的呢?”
“佛法慈悲、道德这身衣服就足够。”
“你总要洗洗澡吧?”
“我的心一干二净,不需要洗澡。”
“你没有朋友,没有爱人,不觉得孤单吗?”
高峰妙禅师指指外头说:“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朋友。”
俗人以为高峰妙禅师的修行是徒然,高峰妙禅师却笑俗人忽视自然的愚钝。花香沁醒心灵,草绿清亮视线,绿荫山峦放松心境,一野果、一掬泉都是原生态的营养。一心参禅,与大自然融为一体,享受清静、新鲜的生活滋味,实在是难能可贵。自然开启人的心灵、陶冶人的情操,久居闹市,心久系名利,人实际上活得很累。荣华富贵、名声赞誉都是表面的东西,月明风清时,人立于月下,会突然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可笑、很荒唐。整日费尽心思与人争斗,得到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烦恼,何必要这样为难自己?
不如将争强好胜的心放下来,到自然的怀抱中沐浴清风,攀登高山,放歌旷野,这种看似休闲、放松的方式,其实是在修心上用功夫。功夫用得不着痕迹,却轻松自然地让心灵放松了戒备,感受到了欣悦。
相比于这种不刻意、不起念的修行,那种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的求取,反而会流于表面、形式,致使努力的人和真正的开悟擦肩而过。
唐朝龙潭崇信禅师,跟随天皇道悟禅师出家,数年之中,打柴炊爨,挑水作羹,不曾得到道悟禅师一句半语的法要。自认为一无所获的他问禅师:“弟子自从跟您出家以来,为什么不曾得到您的开示?”
道悟禅师听后回答道:“自从你出家以来,我未尝一日不在向你传授修道心要。”
“弟子愚笨,不知您传授给我什么。”崇信讶异地问。
师父并没有理会他的诧异,只是淡淡地问:“吃过早粥了吗?”
崇信说:“吃过了。”
师父又问:“钵盂洗干净了吗?”
崇信说:“洗干净了。”
师父于是说:“去扫地吧。”
崇信疑惑地问:“难道除了洗碗扫地,师父就没有别的禅法教给我了吗?”
师父厉声道:“我不知道除了洗碗扫地之外,还有什么禅法!”
崇信禅师听了,当下开悟:禅就是生活,能够自然而然地生活,本身就是一种参禅悟道的修行。吃粥、打扫,看似平常,却像正中靶心的箭矢一样,无限接近修禅之道。能用心静静地聆听生活的不语,领悟其中微妙的禅机,何尝不需要一种功夫呢?
现实生活中的禅法,是将佛法“生活化”,又用佛法“化生活”,在生活中实现禅悦,在禅悦中享受人生,保持一颗本色之心,遇山则高,遇水则低,随顺自然。
迎着每天八九点的阳光,站在窗边手捧一杯醇香的咖啡,看着匆忙的脚步路过街边,有条不紊地开始一天的工作,自是一种徐生慢活的践行;工作八小时中抽一点时间,伸伸懒腰,看看探入房间的嫩绿枝条,放眼被风放牧的天边云朵,紧张的心松弛下来,然后以一种全新的开始继续投入工作,何尝不是一种自然的领悟;工作结束后,不在电视虚像中放空思想,而是手捧书卷,靠于窗边,轻松温读,早早入眠……
以上这些没有任何养生理论的指导,只是佛说“禅宗不立文字,直指人心,似乎有迹可循,却又如月穿潭底,了无痕迹”,所谓修禅、用功,不过是还原生活的原貌,规律、简单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、工作学习。果真这样做了,不经意间遇到花开,微笑会悄然攀上嘴角。



